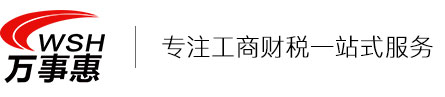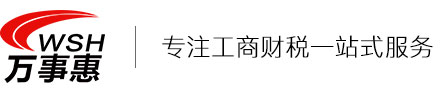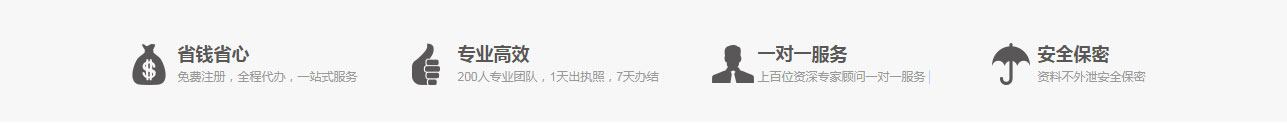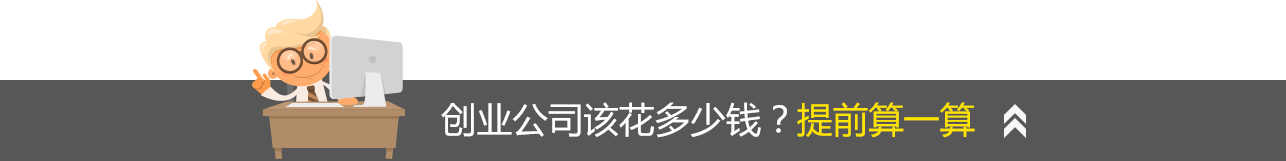人工智能養豬,到底靠不靠譜?
2020-09-02 17:08:32
盡管2019年才是豬年,但養豬的春天已經提前來到。繼網易丁磊養豬之后,阿里也要養豬了。阿里云和兩家養殖集團達成合作,將用人工智能改造養豬業。接地氣的養豬,忽然就和高大上的人工智能走到一起。行業內議論紛紛,人工智能養豬到底是未來,還是炒作?
在我看來,可行性并不是問題。產品落地的關鍵無非是需求和成本:養豬業需不需要人工智能,以及人工智能值不值得用在養豬業。
我們先來了解養豬這個行業。
中國是第一大豬肉生產國,也是第一大豬肉消費國。美國和加拿大這樣的生產大國,也會把大量的豬肉出口到中國。豬肉相關產業在農業產業中排名第一,整個豬肉市場規模超過萬億,是智能手機市場的2到3倍。中國現在的生豬出欄量達到7億頭,就算不考慮進口豬肉,每個中國人每年也要吃掉半頭豬。
所以,整個豬肉市場的容量,完全值得技術和資本的投入。事實上,網易的農業事業部也是經過考察,才在糧食、果木、蔬菜、禽畜等諸多農業門類中,選中了規模足夠大的養豬業。
我們再來看看時機。
網易早在2009年就投入到養豬事業中,卻一度發展緩慢。這和市場環境有很大的關系。盡管市場規模龐大,但豬肉行業和鋼鐵、重工等傳統行業類似,在各個環節上都經過了充分競爭,所以單個環節的利潤率都已經非常薄。
2015年的時候,豬肉價格一度下探到6元以下。這個價格讓養豬變成了一門賠錢的生意,豬場紛紛減產自保。最近一兩年來,環保政策嚴格,原本構成市場主流的小散養殖戶快速淘汰。盡管規模化養殖集團以每年30%的速度增產,豬肉價格也能基本保持在高位。一個萬億級的市場發生巨變,自然會出現大量需要解決的痛點。技術和管理的創新,成為阻礙行業發展的主要瓶頸。人工智能有望解決規模化養殖的很多難題。
就拿養豬中的關鍵指數PSY(Piglets?per?Sow?per?Year?)為例。PSY指數說的是每頭母豬每年生產的斷奶仔豬數。母豬產仔是養殖中最上游的環節,也是各大養殖集團爭奪的制高點。歐美通過精細化養殖,能把PSY指數做到25以上,而中國的平均值在18附近。按照每頭斷奶仔豬300元的利潤來說,這意味著2000元人民幣的收益差距。
影響PSY指數的一個關鍵,是養殖工人判斷母豬發情時的能力。養殖工人會牽一頭公豬經過母豬,然后觀察母豬的幾個行為特征:母豬是否會嗅公豬、身體是否僵硬、陰戶是否紅腫且有分泌物。這些行為特征預示著母豬即將排卵。養殖工人隨后進行人工配種操作。一般認為,人工智能可以大幅提高人工視覺判斷的準確性。
除了實打實地提高PSY指數,人工智能的另外一個使命是代替人工。
中國頂級的養殖集團已經有能力獲得和歐美國家相當的PSY指數。也就是說,這些養殖集團已經觸摸到了生物極限,人工智能技術并不能進一步提高他們的PSY指數。然而,這些養殖集團的高水平養殖是靠人撐起來的。
在這些養殖場中,負責查情的老師傅擁有十多年的經驗。經過一兩年培訓的本科畢業生,往往都還是打下手。查情過程不但需要多人配合,而且耗時長,更讓人員捉襟見肘。人員相關的管理難題,也會隨之出現。只要用技術替代人工,規模化企業才能消除擴張過程中的后患。
因此,即使養豬水平已經達到生物極限,但養豬業依然需要人工智能來取代人工,以便在規模化競爭的潮流中站穩腳跟。
現在,我們來討論另一個關鍵問題,就是人工智能的成本。
近年來,人工智能的發展呈現井噴之勢,這大大降低了技術開發的門檻。人工智能在替代人工的一些應用場景也表現卓越。就拿車牌識別來說,就取代了停車場收費的大爺們。按照這一思路類比,把已經成熟的人工智能技術搬到養豬場,其削減的人力成本,就足以補貼其建設成本。
遺憾的是,這個預期超出了現實。人工智能技術本身是一套方法的集合。在應用方法的同時,除了要嘗試方法組合,還需要迭代嘗試來獲得最佳參數。如果不考慮實際情況,直接套用其他行業案例,那實施者在付出巨大的成本的同時,還很有可能達不到預期的效果。
京東金融去年的“豬臉識別”識別比賽,就向我們展示了問題所在。?“豬臉識別”就是套用“人臉識別”來確定豬的身份。這項技術可以通過識別出的身份來為活豬保險提供真實數據。在知乎上,就有“如何看待京東金融JDD大賽今年舉辦的豬臉識別比賽”的討論。在京東金融官方號的回復中,就列出了“豬臉識別”技術應用的困難點:
1.?豬的生長周期短,外貌變化快,識別難度高。
2.?豬總是運動,很少正對鏡頭,數據采集難度高。
3.?面臨智能耳標等成熟技術的競爭。
就拿采集難度這一條來說。在采集數據的過程中,京東金融派出了20人的團隊,花費了兩天時間,才采集到105頭豬的圖像數據。考慮到大型養殖集團千萬頭的養殖級別,“豬臉識別”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再舉個例子,用聲音識別來分辨產房中被壓小豬尖叫聲,從而防止母豬壓死小豬。母豬壓死小豬確實是小豬死亡一大原因。根據現有的聲音識別技術,識別出小豬被壓也并非難事。然而,小豬被壓超過一分鐘,就很有可能窒息死亡。因此,從識別信號到人工干預,必須在不超過三分鐘的時間內完成。
這種情況下,時間就是生命。一些小豬場甚至會派工人輪流住在豬舍中。工人聽到尖叫即行動,才有可能完成拯救。在這一應用場景中,上行聲音數據的識別,必須和下行干預結合,才能來得及解救被壓小豬。遺憾的是,市場上現在還沒有成熟的自動化干預設備。因此,很難通過人工智能來拯救小豬。
在應用人工智能算法時,豬場很難直接套用其他場景。想要在這方面有所作為,必須同時理解養殖和算法,通過綜合性多種技術方法,創造出低成本而實用的工具。
舉一個例子,京東金融的耳標可以低成本地完成身份識別,但采集到的數據維度太低。把耳標技術和動態追蹤結合,就可以確定每頭豬的位置、行為和狀態。這樣的產品在現階段就有實用性,又免除了養殖企業在盤點和轉圈過程中常見的人工錯漏。當然,即使是這樣一個產品,也需要反復嘗試和迭代,不可能一蹴而就。從這個角度上說,已經習慣了長周期投入的養殖集團們,可能會更有耐心在“人工智能養豬”行業耕耘。
來自:36kr,作者:Vamei,智能養殖領域CTO,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博士,著書《從Python開始學編程》、《樹莓派開始,玩轉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