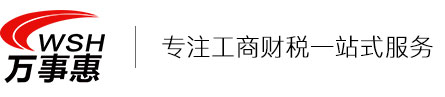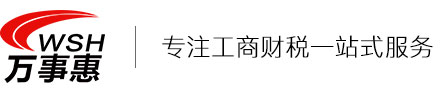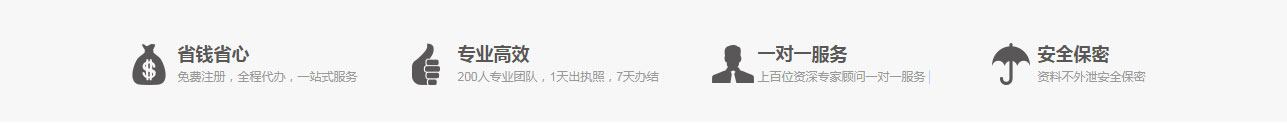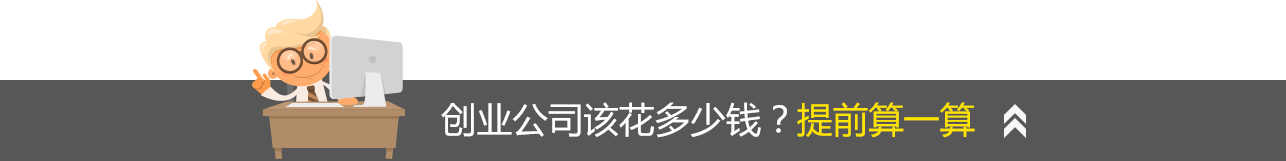第三批自貿區布局內陸開放 著眼風險測試與差異化探索
2020-09-02 17:09:42
第三批七家自由貿易試驗區(下稱自貿區)大局已定,只差鳴鑼揭幕。
3月31日下午,第三批七大自貿區及商務部的負責人在國新辦集體亮相,并介紹了各自的最新進展,同日,國務院正式印發了七大自貿區的總體方案。
第三批七個自貿區將在4月1日集體掛牌,至此,中國自貿區正式擴圍為11個,并形成了“1+3+7”的自貿區開放的“雁行陣”,一個從沿海到中部再到西部的自貿區戰略新框架已初現輪廓。
第三批自貿區是“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等國家戰略中的重要戰略節點與支撐地帶,它們在更廣領域、更大范圍中形成各具特色、各有側重的試點格局。
相對于以往,新一批自貿區更注重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內陸開放被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來,而自貿區向中西部擴圍有利于這些地方更有針對性地探索符合其實際的經驗。
開展差異化立體式探索
3月31日的發布會上,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表示,新的自貿試驗區主要依托發展基礎較好的國家級新區、園區設立,每個都包含3個片區,面積在120平方公里內。
在整體方案設計方面,王受文表示,考慮到各地的差異化,在試點內容上進行立體化探索。
其中遼寧的重點是深化國資國企改革;浙江一項重要的內容就是要通過建設國際海事服務基地、國際油品的儲運基地,來推動對外貿易發展;河南要打造國際交通物流通道,來降低運輸費用;湖北重點推動創新驅動發展和促進中部地區與長江經濟帶戰略對接和有關產業升級;重慶將重點推進“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聯動發展;四川要推動內陸與沿海沿邊沿江協同開發戰略;陜西將創新現代農業交流合作機制,擴大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批自貿區除浙江屬于東部地區,其他六個都屬東北和中西部地區。
王受文表示,這是因為自貿試驗區要向全國推廣復制經驗,如果有中西部地區的,有東北地區的,就能形成一些經驗,進行風險測試,有助于在全國范圍更高層次、更廣泛領域進行推廣,增加試點試驗的針對性。
商務部研究院外國投資研究所副主任郝紅梅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建設具有一定的范圍、具有可控性,其自主開放適用于國內規章,沒有國際上的外部壓力,風險相對可控,也便于壓力測試與調整。”
以外資開放為例,國務院不久前表示,將開放金融、電信、互聯網等敏感行業,這些敏感領域的外資開放將先放到自貿試驗區里進行壓力測試,再推廣至其他地區,中西部的自貿區為這些政策向全國推廣提供了載體。
另一方面,中西部有著更為寬廣的對外開放的空間。以吸引外資為例,郝紅梅舉例,西部地區面積占全國的70%,人口占20%,GDP也占20%以上,然而2016年吸引外資僅為全國的7.7%,而且將2003年與2016年數據對比,可以發現中西部在全國的占比沒有太大的變化,自貿區的設立無疑會進一步開放這些地方吸引外資的潛力。
“內陸開放為中西部帶來了難得的機遇,設立這些自貿區將使其在一些輻射帶動能力較強的限制性產業中先行先試,并逐步放開一些行業的限制,進而帶動當地的發展。”
不過在現實中,中西部面臨著產業基礎較弱、基礎設施有待完善、市場化水平較低、城市化程度較低等條件的制約,在此開展高水平的自貿試驗面臨不小的挑戰。
郝紅梅表示,這一方面需要相關政策的支持,比如必要的財政轉移支付與基礎設施建設;另一方面也需要中西部地區自身加大開放與改革的力度,尤其是努力優化當地市場化環境,降低當地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她強調,在自貿區的建設過程中一定要注意“玻璃門”等隱形障礙,不能“大門開了小門不開”。
對接國家重大戰略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從多位地方官員處獲悉,七大自貿區將在4月1日集體掛牌,至此,中國自貿區正式擴圍為11個,并形成了“1+3+7”的自貿區開放的“雁行陣”。
郝紅梅表示,新一批自貿區由東部向中西部進一步擴圍,其設立大都與國家的整體戰略接駁,在“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等戰略中承擔著重任。
其中,遼寧是振興東北、提升東北老工業基地發展競爭力的新引擎,河南、湖北是中部崛起重要的兩大戰略支點,也是“一帶一路”重要的節點;陜西在絲綢之路經濟帶與西部大開發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而浙江、重慶、四川在推進長江經濟帶發展中起著重要的引領和示范作用。
王受文亦表示,原來國內的改革開放主要是從沿海地區開始,現在國家出臺了一些新戰略,比如“一帶一路”倡議、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為了滿足這些戰略實施的需要,所以選擇了在中西部地區、東北地區設立自貿區。
在上海財經大學自由貿易區研究院副院長孫元欣看來,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建設內容在不斷豐富。“一開始主要是海關特殊監管區、綜合保稅區,2015年把高新技術區、金融片區、高端制造業片區也放入了,如今自由貿易區不僅涉及外貿,還涉及到科技創新、金融發展等方方面面,是一個綜合的改革載體。”
他認為,建設高標準、高水平的自貿區要率先形成一些經濟轉型升級的新模式,比如舟山在建的自由貿易港區瞄準的就是海上供油。“過去是新加坡供應油,現在我們建設的自由貿易區有可能來完成這個業務,并建立了一套服務機制,還可以做海上國際船只的維修。”
孫元欣認為,三批自貿區有一個共同的定位,即兩個“是”和兩個“不是”:自由貿易試驗區是制度創新的高地,不是政策優惠的洼地;是“苗圃”不是“花盆”。
制度創新方面,孫元欣認為,自貿區要和政府組織架構改革結合在一起,比如需要把科技創新和后面的產業化結合在一起,于是浦東新區把經信委員會和科學委員會兩個委員會合并在一起,成立了經科委。
制得注意的是,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周波在發布會上明確表示,新一版上海自貿試驗區方案,將探索大部門制。
商務部研究院副院長李光輝表示,在制度創新的過程中,前兩批自由貿易試驗區面臨的一個共性問題是改革創新碎片化、各部門協同不夠,接下來要以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建設為契機,積極建設高水平的地方政府治理規則體系。
前兩批自貿區此前已經推出了多批在全國范圍內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新一批自貿區也承載著探路的重任。
郝紅梅表示,先前的經驗主要基于東部發達地區的建設,比如上海、廣東等地的管理模式、投資便利化方式;而這并不代表相對落后的地區不能形成可復制的經驗,而中西部地區的試點經驗可能對這些地方更為精準,更符合當地的水平。
“自貿區不止探索可借鑒的經驗,同時也可以總結產生的問題,根據我們近期對‘1+3’自貿區模式的研究,其經驗不乏亮點,同時其難點也有探討的余地,如限制性條款不適應、政策落地缺少保障措施等方面的問題,而隨著試點的增加,探索路徑也在增加,可以有效減少經驗中不完善與有爭議的地方,由此形成全國性的開放格局。”郝紅梅說。
來自21世紀經濟報道
上一篇:2017中國發展高層論壇
下一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中國國際專利申請數量將超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