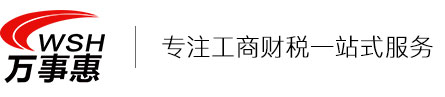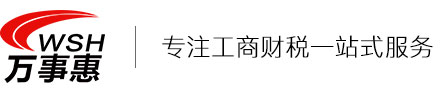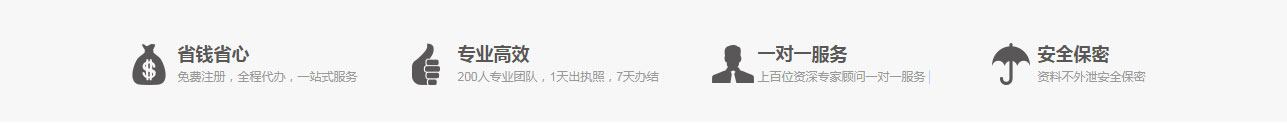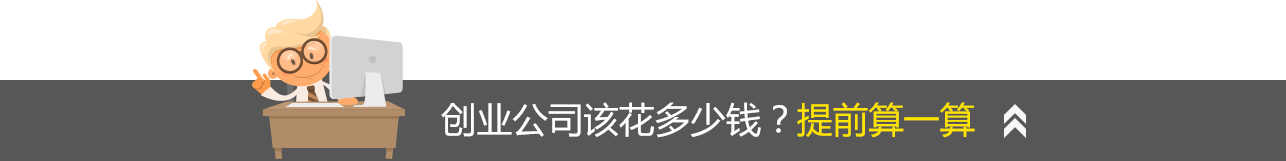中國企業的「IPO病」
2020-09-02 17:09:33
國內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互聯網經濟奇跡:羊毛出在狗身上,讓豬來買單,皆大歡喜。互聯網企業都有相同的套路:先打仗,再結婚,成為獨角獸,最后上市。在這個互聯網公司紛紛合并、BAT插手一切的時代,看似一切都是美好的模樣。
但一次盲目的上市,可能摧毀你多年來辛辛苦苦建立的一切。特別是在企業上市前的IPO(首次公開募股)階段,這是一次全裸出鏡,在公開的放大鏡中,任何一個弱點,都會被快速捕捉,成為致命傷口。
燒錢!燒錢!再燒錢!
5月4日深夜,永安行董事長孫繼勝和中介機構爭論到半夜,最后首次IPO還是暫緩,作為外界嘴中的“共享單車第一股”,永安行上市計劃早已被炒得沸沸揚揚。
永安行是公共自行車業的“隱形巨頭”,入行早、覆蓋廣、業務多樣化、運營經驗豐富、政府資源多。其公開資料顯示,共享單車模式毛利極高,達到驚人的92%,堪比游戲行業,2016年永安行凈利潤達到1.16億元。
2016年,自行車行業出現了新鮮血液,以摩拜和ofo為代表的各色共享單車,涌現遍及一線城市街頭。進入共享單車市場不到兩年,摩拜和ofo就成長為獨角獸。公開資料顯示,兩家融資額合計超過10億美元。
這是一場跑不贏就死的道路。不可避免,摩拜、ofo和永安行,共享單車領域的三大巨頭,將燃起持續的燒錢和商戰。通過大量補貼,然后投放上億規模的單車,以換取市場份額,上演滴滴和優步、美團和點評、優酷和土豆的過程和結局——先激烈地干一仗,然后就突然結婚。
不得不承認,如今的商業競爭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演變成一場燒錢競爭。對于更多的企業而言,錢不是問題,問題是沒錢。
傳聞有很多:比如,宏磊股份曾債務總額一度高達25億元,其中包括大量民間借款,如果上市失敗,八成已經破產;溫州最大的眼鏡企業浙江信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負債20多億元“跑路”,背后是擴張太快,資金鏈斷裂,新公司想上市未果。
在業界,有這樣一種言論:最近幾年上市的公司中,有40%的公司如果不上市就倒閉了,這就是它們沖刺IPO,不惜一切代價鋪路的原因。
然而,錢真的不是問題嗎?四次闖關IPO,神舟電腦雖然擠進了上市的大門,但市場質疑之聲不斷:在PC產業毛利逐漸降低,增長乏力,高端品牌價格下沉擠占低端市場情況下,神舟電腦既缺乏創新能力,價格優勢也在逐漸消失,低價模式難以為繼。
IPO成功與否,決定了這些企業的命運,并不是這些企業上市能為投資者帶來什么好處。三只松鼠、美團這些互聯網基因的企業,正在全力沖刺IPO,上市仿佛是拯救企業的唯一法寶。然而,最后將成為企業的“救命稻草”還是“致命毒藥”,還存在著極大的變數。
IPO是一種病
中國企業總有一種IPO情結,或者說是一種IPO病。
在“資本狂躁癥”的催動之下,企業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財務造假、過度包裝、盲目擴張、八方舉債,哪管身后洪水滔天。
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這種“不懷好意”的企業,一旦上市,往往是股價一落千丈,高管套現離場。
關于這樣的案例太多,十幾年間,殞命上市途中的企業可以羅列一個長長的名單:家世界豪賭上市未果,被迫出售資產;太子奶簽對賭協議控制權易手;最大的印染紡織企業浙江江龍,為上市被天量債務壓垮;萬德萊盲目改變主業迎合上市,最終被市場拋棄……這些“巨頭”紛紛折戟沉沙,讓IPO正演變成一條“不成功,便成仁”的道路。
是什么吸引企業前赴后繼的奔向IPO?在巨大的IPO“蛋糕”背后,是一條貫穿整個IPO進程的利益鏈。
IPO中介中投行是主角,會計師和律師是配角,陪著投行闖蕩江湖。券商負責全面協調,會計師負責審計,評估師負責評估,律師負責法律事務。
有個笑話講,在IPO業務中,投行負責忽悠人,而律師和會計師就是負責告訴別人,券商忽悠你的話都是真的。這樣的比喻十分傳神。
除此之外,PE是IPO過程中不可忽視的另一大力量。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涌向PE,是因為實在太吸引人。假設用1億元資金平均投資10個項目,一個項目1000萬元,最后只要有2個項目成功上市,投資回報若為20倍,2個項目收益為2億元,1億元投資相當于還賺1億元,這就是我國PE的特點。
在IPO暴利時代下的生態鏈,是這樣串成的:最上游者為實業資本、天使投資、PE/VC、突擊入股者等;中游為各類中介機構:券商投行、會計師、律師事務所和咨詢公司等;下游包括一些媒體公關、打新機構等;直到最末端的就是最后接盤被割肉的散戶們。
別讓企業倒在最后一公里
不是排隊,就是在去排隊的路上。對于大多數企業而言,IPO是一個艱難而漫長的過程。
首先,企業在向證監會提交材料前需要經過三年的輔導期,還要向機構支付前期費用,為上市進行各種調整也需要支付巨大而無形成本。不到萬不得已,甚至難以彌補的漏洞,企業是不會在臨門一腳的時候退出申請。
僅從流程來看,就有聘任中介服務機構、盡職調查、企業改制、輔導備案和公告、股票首發分受理、見面會、問核、反饋會、預先披露、初審會、發審會、封卷、會后事項、核準發行等數十個環節。
在發審委階段,每年過會企業將近300家,上會通過率約達70%~80%,而進入初審中的企業達到700家,證監會已經受理的企業早已超過1000家,按照目前的IPO速度,一半以上的企業走不完上市之路。
而企業主要被否的原因,集中在這幾點:1.關聯交易與同業競爭;2.未來盈利能力被質疑;3.企業無法解釋募投項目所規劃產能未來消化能力;4.申報企業財務數據真實性及其他信息披露質量;5.企業違反社保、稅收法規等方面。而事實上,任何一點小小的瑕疵,都可能成為企業折戟沉沙的命門。
除此之外,在IPO過程中,企業往往十分低調,是害怕背后的眼睛。其中,“舉報信”和“媒體曝光”這樣的質疑性字眼,往往成為企業的攔路虎。例如,創業板開閘以來,證監會創業板部共收到300多封舉報信,涉及100多家企業,這意味著超過一半的上會公司曾經被舉報過。
按照《蒙牛內幕》一書中蒙牛公司的說法,在蒙牛上市前夕,公司接連遭到誣陷。其主要競爭對手的液態奶部門相關負責人,向北京未晚公司支付490多萬元,令其散布對蒙牛不利的謠言。公安機關查實,在其所實施的5次行動中,全國11個省會城市的平面媒體及網絡發表了上百篇詆毀蒙牛乳業的文章。
在進入上市程序的企業身上發生的一系列危機,得到一個證明:一家原本不太惹人關注的公司,可能因為上市而瞬間卷入危機事件。
要么致富,要么出局
風險投資模式的基礎是為投資者創造財富,而非打造成功的企業。
作為創業者,在面對風險投資人時,對方總是將改變世界掛在嘴邊。你要相信,商人都是逐利的,他說的十有八九都是“順嘴一說”,他們的商業模式很老套:低買高賣。
從入股到退出,風險投資機構對一家企業的投資周期通常為5年,他們希望從中獲得數倍甚至數十倍的回報。在此之后,公司會是立刻倒閉還是基業長青,便與我無關。
上市的確是在與“魔鬼做交易”,這會迫使企業擁有者以犧牲長期增長為代價,專注短期股價波動。公司的控制權也會從創始人,轉移到成千上萬素未謀面的股東手中。
比如Zappos。CEO謝家華希望保持對公司的控制,但以紅杉資本的麥克·莫里茨為首的投資者卻另有想法。2009年,由于擔心Zappos的現金流,他們開始對謝家華施壓。“如果業績不改善,董事會就會炒了我,然后任命一位一心看重利潤的新CEO。”結果,謝家華決定將Zappos賣給亞馬遜。他認為,與被投資者掌控的董事會相比,亞馬遜是一個更好的管家。謝家華或許阻止了董事會的“陰謀”,但卻犧牲了公司的獨立性。
另外,關于與“魔鬼做交易”,國內企業在IPO過程中隱含對賭協議,已不算新聞。如此前轟動一時的太子奶事件——在資本和盲目發展的雙重誘惑之下,太子奶吞下了“對賭”的苦果。
“對賭”其實屬于正常的商業行為,正面會給企業帶來激勵效應,但往往有些企業引資心切、過分樂觀、不切實際地去“豪賭”,最終往往落得被迫出局。證監會要求,IPO企業若存在對賭協議,必須在上市之前清理干凈。
對資本的誘惑,企業是否接受對賭,要根據自身實際慎重決定。逐利是資本的天性,一旦將來企業發展未達預期,這些風投將毫不客氣地履行對賭協議。
寫在最后:小心背后有炸
太差的企業上不了市,太好的企業又不上市。
對于許多準備沖刺上市的企業來說,IPO的游戲規則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嬗變過程。然而在此過程中,千萬不能有僥幸心理,須按法律逐條規范行為,逐一排查“地雷”。
上市是企業的新里程碑,不是企業家盲目的一時率性,小心有炸。企業上市的“地雷”,包括運營模式、競爭優勢、資產質量、盈利能力、公司治理結構、未來發展前景和企業抗風險能力等。這些問題難以被量化,在發審委的通過與否決之間,存在很大的變化可能。
在遭遇上市“地雷”之前,企業首先要做的,就是回答企業上市動機這個最基本的問題:企業為什么要上市?什么時候上市?上什么板?融資多少合適?這些問題看似簡單,其實并不是所有的企業都能回答。很多企業上市,背后的情況往往是投行、券商看好一個企業,把它推向險象環生的資本市場。
俞敏洪曾說,他后悔讓新東方上市。其實從綜合角度來講,上市的好處很多,但是規范化和透明化,往往讓企業走得唯唯諾諾,不差錢的公司真沒必要上市。
本文來源于微信公眾號快刀三俠(ID:iyqkpd),商業快媒體、思維孵化器、價值試驗場和洗欲中心。